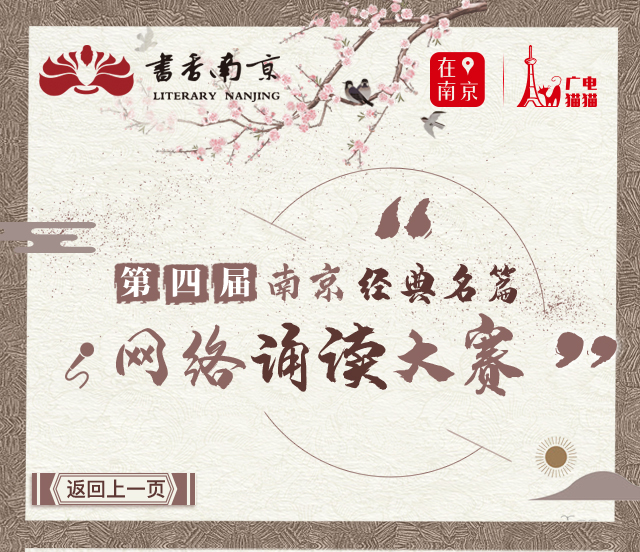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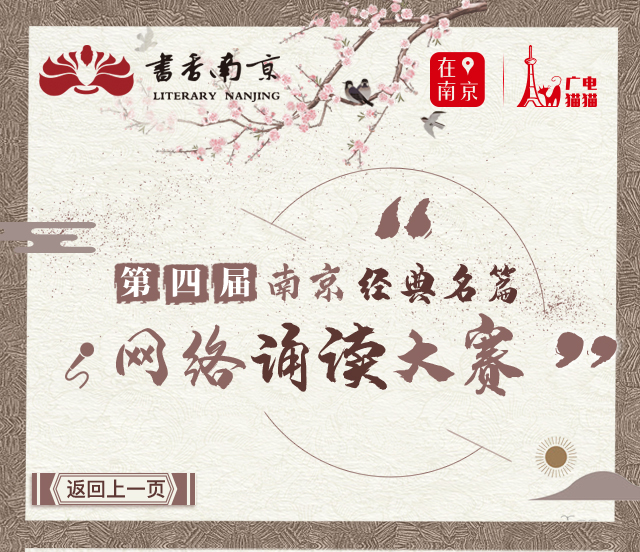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肖复兴】
八十年代,我常常到南京去,有时一年去好多次。那时候,南京是我除了北京之外最熟悉的地方。现在想想其中的原因,大概在于那时候的南京文学活动特别的繁盛,《雨花》《青春》和《钟山》成为了那时全国文学的重地,第二届全国文学奖的颁奖大会,也是那时热热闹闹在南京召开的。而且,我的第一篇写南京击剑女将栾菊杰和她的教练文国刚的报 那时候,《雨花》主编是顾尔镡先生,他打来电报要我到南京修改这篇稿子,我第一次来到南京,走近总统府《雨花》编辑部,它的旁边是太平天国的一个漂亮的花园, 正是夏天,花园里花繁叶茂,生机勃勃,那时候,文学也是这般景象,和现在的颓败完全两个样子。我就是在这个总统府里,第一见到了摇着芭蕉扇的顾尔镡和铺一张凉席躺地上午睡的高晓声。在我的回忆里,那时候的文学也就像这样的平易,作为一个普通的投稿者受到如此的礼遇,只能发生在那时候,现在则是完全不可想像的。
我就是这样走进了文坛,南京扶亲切而平易地扶我迈上了第一个台阶,我对南京始终充满感情。
参加第二届全国文学奖颁奖活动那年,我和张承志、郑万隆一起来到南京,一起去看望张弦。是郑万隆的提议, 那时,他在《十月》当编辑,和张弦有稿件上的往来,便比较熟。我是第一次见张弦,但读过他当时有名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文革之前还看过他编的电影《上海姑娘》,也算是他乡遇故知。郑万隆虽和张弦认识,但并没有来过他家,凭着一纸地址,我们找了好半天,才算找到,在一条小巷子里,是间并不大的房子,张弦和他当时漂亮的妻子见到我们的闯入,很高兴,一副相见恨晚的样子,立刻拉我们到外面吃饭。那顿午餐吃的什么忘记了,但那情景很难忘,是在中山路上一家西餐馆,二楼的餐厅上,非常安静,幽雅。张弦特意要了一瓶威士忌,张承志也非常懂行的要了一些冰块加进酒中,而我则是第一次喝这洋酒。席间,张弦频频为大家添酒,其实,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了。张弦死得太早,否则他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来,现在走在南京的大街上,知道并记得张弦的人还有几个?也算是应了那句古诗:文章千古名,寂寞身后事。南京的街景现在越来越繁华了,而文学的景象和气脉却大不如以前了。这也许就是时代的发展的一种必然吧。
八十年代,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是1988年的秋天,南京的朋友特意带我们去苏州池阳澄湖的螃蟹。那一次,在从苏州返回南京的车上,我和叶至诚先生正好坐在一起,便聊了一路,向他讨教了许多东西。那时,他正在《雨花》主编的任上,此次活动,他也是组织者之一,一路很辛苦,却对我百问不烦,说起了当年他和陆文夫、高晓声、方之因组织“探索者”而蒙冤的岁月。因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读过方之的短篇小说《岁交春》,很喜欢,留下很深的印象,便向多问了几句,他总是非常耐心地讲给我听当年的情景。那时候的文学,真的很让人怀念,因为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是那样的真诚清澈。
如今,八十年代已经远去。叶至诚先生前些年就已经去世,前些日子,他的哥哥叶至善先生也溘然仙逝。日子仿佛老去的那样快,八十年代的南京,如同一副色彩有些斑驳的老画,只是有些伤感地悬挂在我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