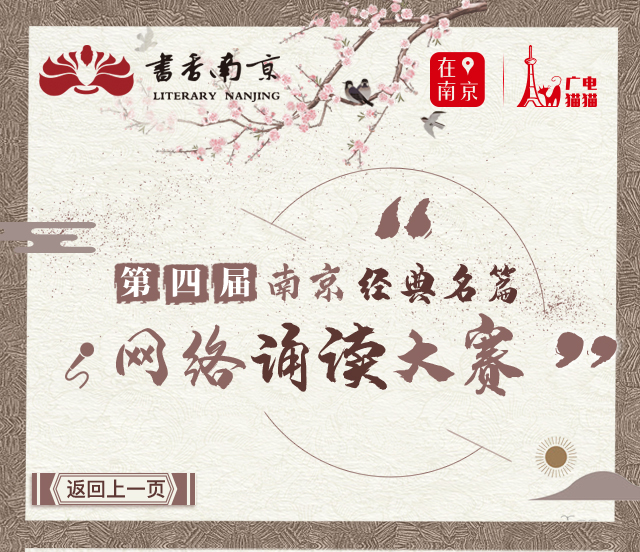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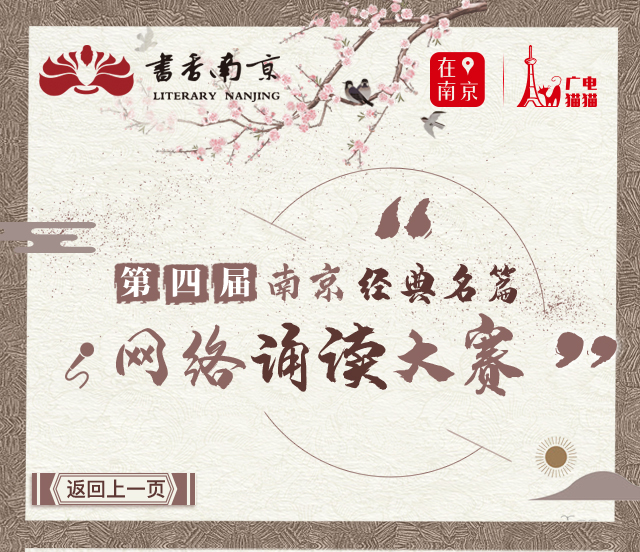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俞律】
(本篇选自《秦淮恋》,作于1988年8月。作者俞律(1928-),江苏扬州人。作家。著有《湖边集·俞律小说散文选》《萧娴传》《浮生百记》《菊味轩诗抄》等。
秦淮河边,夫子庙旁,有一条因科举制度而得名的贡院街。它蹉跎过多少有为和无为的岁月!作者以此为背景,写了五十年代初“观舞观棋两个平淡无奇的旧事”,反映了新旧社会交替中的世态变迁和人生沉浮,并寄寓他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同情。)
一条街而以“贡院”命名,弄得古里古气,才沾得神秘色彩。这几年市府花了一笔大钱,把破旧的沿街楼馆哗啦啦都拆了,我起先颇为担心这是现代化的前奏;后来听说拆了旧的,还要建起更旧更旧的,这才放下心来。倒不是我嗜古成癖,而是“古”对于任何文化人都是一个介于知与不知之间的怪物,并不比未来明朗多少。不知其底细的事物是最诱人的。
我颇想在贡院街的旧貌还不曾变为旧旧貌的时候,去看一次它东头的四十七号。我从1953年起,就生活在这个陈旧的大院里,一共度了十五个春秋。“十五”是个戏剧性的数字,京戏四郎探母不是哭着唱“弟兄们一别十五春”的么?这里头很可以觅到一点创作灵感的,写点什么下来,让后人知道一点个中底细也是好的。然而建设速度出奇的快,那四十七号已被夷为平地。新的仿古建筑马上就是在这个废墟上簇拥出来,倒又使我不无惆怅了。
这里在1952年以前本是热闹的秦淮旅馆,两层的楼房,那格局就像演三十年代故事的电影里的旧式客栈。楼下一个方方的天井,客房密匝匝地围住这块摆布着老人脸上皱纹似的裂缝的洋泥地。大门入门处有一架还算宽敞的木楼梯,走上去便站在有点摇晃的楼板上了。楼上客房还是那样围住天井,把蓝色的天也围成了一个小方块,看上去天也是这个旅馆的一部分呢!
其时交通银行看上了这幢房子,花了一笔钱买下来作办公用房了。过了两年又搬到太平路去办公,这个贡院街四十七号就留给职工们安顿蜂房似的小家庭。
这里坐落在夫子庙最热闹地段的最东头,紧对过是解放电影院;东面就是拥有大光明戏院的那条街;西头嘛,永安商场日夜挤满了人;再朝西乃是横跨在秦淮河上的黄公桥了。
老实说,四十七号本身并没有什么落花流水之恋,它之所以时时引出“死生亦大矣”之感,却在其东头的凤凰舞厅和西头的黄公桥。
说到凤凰舞厅,它不过是个小小的略有点放荡的娱乐场罢了。其址在解放电影院之东,隔街相望。每天晚上,一阵阵舞乐总是蓬蓬拆拆地传到那个四十七号里去。
我虽说是上海洋学生出身,当年在十里洋场却是从来不涉足舞场的,舞厅于我本无任何诱惑力。只是由于初到南京,家眷又不曾带着,难免常有异乡的寂寞感。到了晚上,有时真不知如何措手足。有一次竟被那舞乐声引着,踏进凤凰舞厅,看看凤凰到底是种什么鸟。
舞伴相拥,款款然以优雅舞步抒发爱慕,倒真是一种艺术。我平生不入舞池,只得作壁上观了。舞池里的灯光真像水一般地流动着,舞者如鱼,自得其乐;而观舞如观鱼,个中境界,大有庄子的哲理在。
这是秦淮河畔特有的风情。这里的舞者的确比上海的土,但这种土却是秦淮水浇灌着的,可以在其中物色到秦淮色彩的诗。
我观舞只是为了读这种诗。本以为这是我独家风范,想不到后来发现,近处又有一位沉默的观舞者。
这是一位约莫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眉宇间浮动着楚楚动人的秦淮乡土气。我那年实足二十五岁,但遇到的却不是个罗曼蒂克故事。我只是逐渐注意到她,而她似乎完全不注意周围的人和事,她的呆滞的眼神自然不会触及我的存在。只有这么一个月光淡淡的春宵,我偶然走近她,她才望了我一眼,摇头说:“我早不跳了!”当时还弄不清她的意思,后来才从某些知情人口中弄清她过去是个当舞女的,于是明白过来,她常来此地大概是寻找某种失落吧?
四十七号周围一带原是旧社会吃喝缥赌场所的集中处,它的南面就是名声很不好的石坝街。从北向南穿过黄公桥,马上就进人当年的烟花巷陌了。暗中度神女生涯的,到1953年还未绝迹。那时交行有一位干部,就在其地被一位神女拉走,不免落了笑柄,同事们老跟他开风流性质的玩笑。
当然舞女和妓女总还隔一层,何况这观舞女郎十分质朴,全然的脂粉不施,绝似良家妇女。至于她失落了的究竟是什么,我也无从打听。从年龄判断,也许她失落的是爱情,这可不是别人可以补偿的,故而也就不想找她搭汕。后来却悔了:也许我当时错过了一篇动人小说的情节。
夏天来了,秦淮河泛起草腥味。一天中午黄公桥上有人喊“救人!”原来有个女人翻过木桥栏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等我悟到了一点什么,三步两步跑到桥边,一切早已过去。秦淮河依旧静谧地让午风吹起微皱,桥上站着几个木然的男人和女人,扶着栏干向水里瞧。我于是便疑惑跳水的就是在凤凰舞厅仿徨的那个秦淮女郎。晚上竟再也不想观舞去了,怕果真应了我的疑惑。一连多日,虽不得安寝,都也有点轻松感—这似乎可以象征一个时代的消失的。
以后,我经常晚上到黄公桥上去看逝水,看水里微微颤动的流不掉的秦淮月,希冀遇到使人喜或愁的事。
黄公桥是木结构的,其时已是年久失修,踏脚上去,似乎都有点心理的摇晃。所以过了几年便被拆光,另建了石桥,连名字也一并换成了“白鹭”。然而我喜欢“黄公”这个桥名,因为我在这桥上,终于遇到了很喜的事。我就在心理的摇晃中结识了一位沈先生,他是一位奇人,一位象棋高手。尽管“黄公”和“黄石公”完全风马牛,我偏觉得自己充当了年轻的张良这个角色。后来的许多良宵便混迹消磨到夫子庙旁的象棋摊上去了。
将士相车马炮!坐暖了屁股,输一盘棋只花一分钱。我有时一晚下四、五盘棋,虽是输得多,却也颇学得一点棋艺。
沈先生说,从前夫子庙棋摊出过大杀手万启有,打遍秦淮无敌手,连扬州三侠窦国柱、张锦荣、朱剑秋都不放在他眼里。他收过好些徒弟,沈先生就是其中一个。
在棋摊上混长了,就结识了当时两个南京最辣括的棋手,一个瘦小的高源林,一个壮大的印邦春。那时他俩已入中年,高君在某个纱厂做工,印君则在秦淮河的内桥角上开一个小饭店。
一入局中,便会着迷。我把《橘中秘》《梅花谱》等一一研究摆布,又到南京文化宫象棋组混混,参加《象棋月刊》编辑,一本正经地为高、印二君和沈先生写文章立了传。
记得是1954年春天,黑龙江棋手王嘉良和北京侯君来宁比武,文化宫安排高、印二君应战。人家王嘉良十分的年轻厉害,一阵把高君杀败;印君也输给了侯君。那天我任副裁判,便劝王君再另杀一场。棋迷们又起哄,把沈先生捧上台。我起先以为沈先生年纪大了,斗不过人家东北名将。谁知他老先生胸有成竹,执黑先行,第一着来了个“象三进五”。台下交头接耳,议论起来,想是笑沈先生走了软着。殊不知一路杀下去,沈先生竟逼得王君订了城下之盟。那几年我涉足棋坛,看了不少精彩好棋,观棋之乐,比观舞又要深沉得多。
又过了几年,这一切都夹在黄公桥下流水中东去了;然后便是“文革”,贡院街上一片“打倒”之声。又谁知历史是全然打不倒的,这一切不又回到我的笔端来了?
每读《儒林外史》,总被周进哭贡院的故事弄得忍俊不禁。这周老头儿真想不开,只想向庙堂之高爬去。其实江湖之上有的是高人、贤士、奇女、真男,这十里秦淮,真才真艺是消磨不尽的。我这回信手书来,虽只写了观舞观棋两个平淡无奇的旧事,却也伴得江左烟霞、淮南首旧,留一段野史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