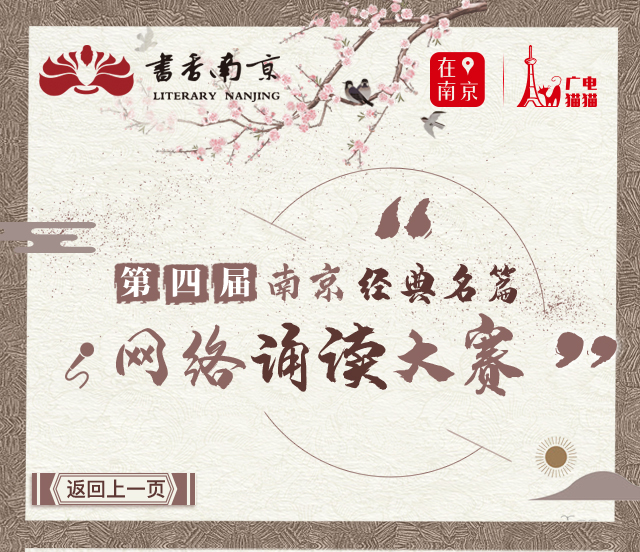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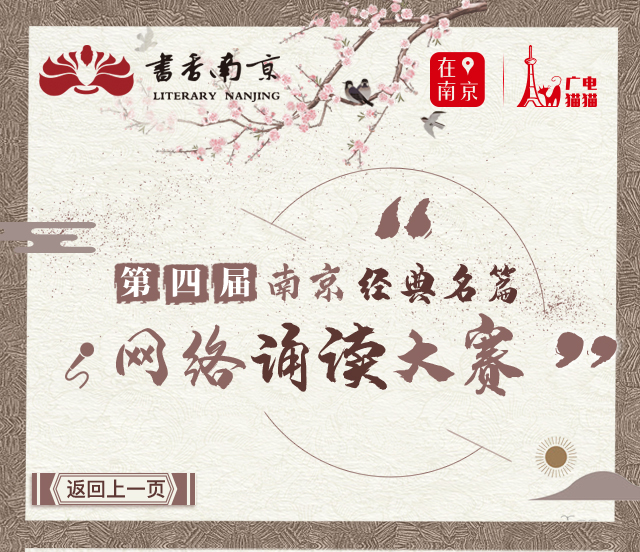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袁鹰】
(本篇选自《南京大观》,作于1993年。作者袁鹰(1924-),江苏淮安人。诗人,散文家。著有诗集《江湖集》《花环》《袁鹰儿童诗选》等。
作者是江苏人,对省城南京有特殊感情。本文从“六朝烟水气”的定义和内涵谈起,说到南京的自然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言辞恳切,例证有力,显示出大家风范。)
若问起对南京的印象,只觉得五味杂陈,一言难尽。说到南京,我总怀有游子思念故匿的依恋之情,虽然我并不是南京人,也从不曾有一次在石头城里连续住过半月以上。我说不清那种亲切感温馨感从何而来,如此深深地吸引着我的是什么。是长江的浩淼、钟山的巍峨,还是玄武湖的清丽、莫愁湖的秀美?是雨花台的肃穆、中山陵的恢宏,还是秦淮河、新街口和鼓楼的繁华?然而,浩淼的江河,巍峨的山岭,五彩缤纷的园林,庄严肃静的纪念地和繁华的街市,不少大中城市都有,何以独独钟情于南京呢?
万千思绪中,忽然想到《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中那位天长才子杜慎卿过江来南京,同友人徜徉雨花台岗上,“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茶,回来再到雨花台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何为六朝烟水气?吴敬梓未作诠释。他在南京住了多年,不仅同文人交往,也结识些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耳濡目染,熟悉当时南京的风土人情。随意点染几句,就给南京和南京人添一抹淡淡的高雅色彩。这“六朝烟水气”,闲闲五个字,却很耐品味。若要去寻觅,谁又知道它在哪里呢?仔细想想,界定虽然有点模糊,却非在虚无飘渺之间,倒也是实实在在的。
几年前在南京与艾煊同游夫子庙。当时正值市政当局大规模整修夫子庙。我们一边东张西望,一边随意评说。他对新修的那些仿古建筑漆得金碧辉煌,甚至银行门前挂上旧时钱庄店招和古钱标志,很不以为然,认为是不伦不类的标志。我说这夫子庙一带本是文物荟萃的所在,多一点文化气氛才是。他叹口气:“有些人太热衷追求六朝金粉了。”那些史籍和古诗中渲染的“六朝金粉”,多半是指朱门豪户的笙歌院落、灯火楼台,歌楼舞榭的酒色征逐、风月繁华。这在晚唐的杜牧夜泊秦淮时,看到的就已是荒烟寒水,连一点金丝粉屑都不见踪迹了。那么在今天还何必苦苦地追求呢?
六朝烟水气,我想,至少可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生态的爱护、维护和保护,二是文化氛围的酿造、营造和创造。
南京很有点得天独厚。虎踞龙蟠,气象万千,青山隐隐,绿水迢迢,逶迤的重峦叠嶂,“白下有山皆绕廓”,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世世代代的南京人,又在山山水水间加上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的绿,厚厚的浓浓的绿,初次来南京的外地人,一下火车一下飞机,立即会惊喜地发现自己浮泅在绿色的海洋里。我第一次到南京还是在少年时代,离现在已近六十年,当时唯一留在脑际的,一是中山陵,二是林荫道,此外就一片迷茫,记不真切。近二三十年来多次去南京,绿的印象依然最深刻。每次听到南京又兴建一座高楼新厦的消息,就不无杞人忧天地担心那厚厚的浓浓的绿。韦庄当年在金陵有诗云:“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那是诗人对六朝如梦的感喟,其实台城柳总是有情的,只要人不去破坏它,它总是呈献给你十里烟笼。
解放后初次去南京是在1962年,承章品镇等几位同志盛情相陪,得以从容地游览南京城内外多处胜迹。当时正值金秋时节,栖霞山那一大片枫叶如丹,比北京香山的红叶更加壮美明艳,使人有惊心动魄之感。转到千年古刹栖霞寺后殿,看到一副楹联,可惜未曾抄,只记得下联有“风霜红叶经……数江南四百八十寺,无此秋山”之句,不仅有诗情画意,而且烘托出一片宁谧幽深的境界。十年浩劫,不知这副楹联还留在人间吗?如果被砸毁,有没有修复呢?
南京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一部多姿多彩的诗文巨著。从三国吴大帝孙权到民国的蒋介石,十个朝代先后建都。虽然它们都是短命的,来去匆匆,繁华转瞬,“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十个朝代加起来不足四百年,时间跨度却经历了十几个世纪,每个世纪都多多少少留下脚印。如果说有的千年旧都、文化名城被厚厚的尘封积垢掩盖,有如褪了颜色、帙页残损的线装古籍,南京就是一套具有现代装帧设计的新版系列巨著。打开这套书,一卷卷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便展现在眼前。有的浑厚,有的秀美,有的凝重,有的轻盈,铁板铜琶,红牙细管,使你目不暇接。到中山陵,到雨花台烈士陵园,到梅园新村,煦园、瞻园,犹如读一部历史;到莫愁湖、燕子矶、牛首山、白鹭洲,如读几卷诗词歌赋;到鸡鸣寺、北极阁、乌龙潭、天堡城,又像看几页笔记小品;走过那些冠以南京古名的秣陵路、建邺路、建康路、白下路、朱雀路、虎踞关、龙蟠里……只要偶尔一瞥路牌,也自会呼吸到一点文化气息。那乌衣巷口,桃叶渡头,自然早已不见当年的一丝痕迹,却也能引起你一点遐想,几缕幽思。
有一回同一位老友在濛濛细雨中上清凉山,踩着被雨水冲洗得十分明净的石径,来到扫叶楼。室外有林散之老人手书石刻,室内陈列着龚贤的遗物和画幅。除一位工作人员在闲坐看书外,只有我们两个游人。步履迟迟间。仿佛听到那位半千先生悲怆低吟:“登眺伤心处,台城与石城。雄关迷虎踞,破寺入鸡鸣。一夕金笳引,无边秋草生。橐驼尔何物,驱入汉家营。”缅怀故国,憎恶异族统治的愤慨之情,使我想起南昌青云谱八大山人旧居。这两位画家是同时代人,遗民心境是相通的。我说:“这种气氛和环境,别处很少见。”友人答日:“南京倒还有几处。不过,可能也因为今天是下雨天。”是的,若是晴天,来领略“扫叶人何在,登楼思悄然”情味的人也许会更多些吧。大路旁尽可以去开饭馆酒楼歌厅卡拉0K电子游戏室,满足各色人等的需求,让这里长久地保持一份清凉、清净、清幽,有多好啊!
前些时消息传来,说雨花台下有人在筹办狗展。近年狗忽然变成了宠物,善男信女对它顶礼膜拜,视为至宝,想发狗财的人趁机展览名狗,自然都有他们的自由。但是一想到雨花台烈士的英灵整日整夜将被唁唁然嚣嚣然的犬吠声惊扰,顿时有点不寒而栗。幸而,南京人及时制止了这件荒唐事,保持了雨花台的肃静安宁,这虽是小事一桩,却多少显示了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力量、舆论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今天,到雨花台去看落照的南京人未必有几个,但是要想大吹大擂招引人去雨花台看狗,即使是身价高昂的洋狗名狗,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多数人赞同的。
六朝烟水气有了新的内涵,得到新的升华,使我忻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