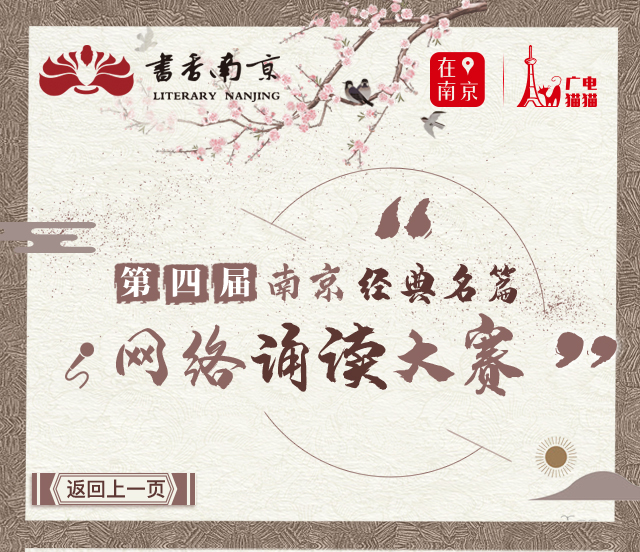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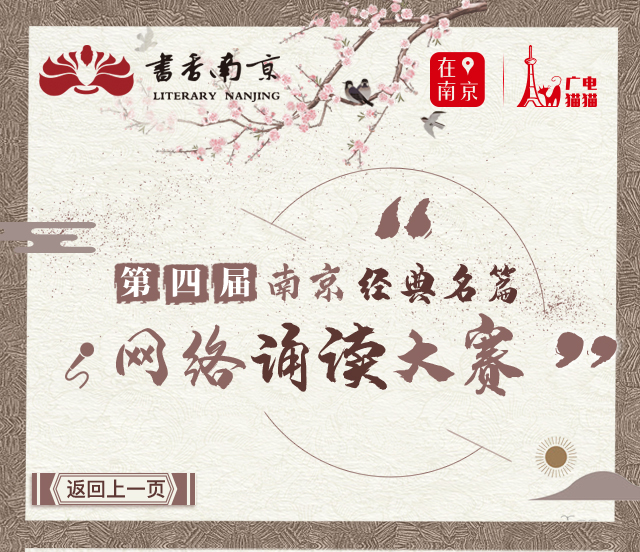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陆华】
(本篇选自《扬子晚报》( 1994年3月16日),作者陆华(1939- ),江苏盐城人。作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散文集《名人·风情·掌故》等。
如果把南京古城墙比作一部宏伟壮丽的史诗,那么六百年前建城时来自长江中下游三十个府一百多州县数不清的城砖,就是组成它恢宏结构和丰富内涵的一个个“方块字”。作者通过个别局部的仔细考察,犹如全息摄影,让我们看到了创造这一人间奇迹的“历史的真正的主人”。)
一次会上,听南京市文物局陈局长说,一块南京明代古城砖在美国值200美金。我心里一“咯噔”。明代城砖,在咱南京城里,岂不是所在皆有,谁把它当回事了?可细一想,是不该轻慢了它;那朱元璋动员20万人花了20年时间“高筑墙”,襟江带淮,蜿蜒30余公里,是世界城垣之最呢。想200多年前当华盛顿得意洋洋地将第一面星条旗升向北美大陆天空时,我们的南京明城墙已在历史风雨中屹立4个多世纪了。难怪我们一块砖头,就把美国佬给“镇”住了!
进得家门,就直奔阳台,记得那里角落里有一块便是。那是家里人从路边捡来垫物隔潮的。出了一身臭汗,把它从旧桌肚下的杂物堆中掏了出来,又清洗了一下,剔除遍体的粘着物,算是像模像样了:端的是标准的城砖,明代的;虽说两只角是残缺的,又几乎断为两截,但总体还算完整,特别庆幸的是两侧铭文比较清晰。
用皮尺比划着量一下,与史料所载完全吻合:长42厘
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从断层处细究,呈青灰色的砖体相当密致硬实,用小铁钉使劲刻划,只成浅痕,和我们在工地上常见的那种酥松易碎的砖块全然不同。砖体粘着物为纯白,有点像岩洞壁上的石钟乳,为剔掉这些“石钟乳”很费了些劲,须用螺丝刀一点一点地撬;看来这就是史料上所说的当时砌砖所用的一种砂浆了,这种粘合力极强经久不坏的砂浆究竟是用哪些东西合成的,至今还是个谜,有说是用石灰、糯米汁掺以桐油,也有说是秫米糊或蓼草什么的加石灰再掺桐油。
不过我十分感兴趣的是铭文。史料上说,当年朱元璋
为建造都城,下令长江中下游的五省30个府的100多州、县,大量烧制规格划一的城砖。为了保证质量,这位贫苦农民出身有丰富生产劳动实践经验的朱皇帝,出了个奇招、绝招,规定每块砖上都得印字,哪里出的,谁监制的,制砖的工匠是谁,窑工又是谁,砖上记得清清楚楚。可以想象,如出了质量问题,指着上面的名字追查下来,谁赖得掉?怕只有“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的份儿了。现今到处在讲责任制,条条杠杠一本本的,我想可能都不如那老朱的厉害。下面我来具体介绍一下铭文内容。一侧的文字为:临江府提调官同知张著 司吏陈鉴
清江县提调官知县王贞司吏刘显德
另一侧为:
窑匠芦志民
造砖人夫付原方
诸位看得明白,就这么一块砖头,涉及的责任人竟有9
位,都是600多年前的有姓有名的人啊。他们是临江府(明初设置的今江西省清江县一带的市级官府)负责贡砖的官员张著张大人和他的助手陈鉴先生,所辖清江县负责贡砖的官员及其助手王贞、刘显德。这些是两级官府负有领导责任的责任人,属于“上大人”之列,他们占了一侧的位置。另5位屈居另一侧,属于平头百姓了,他们是乡村三级小头目付允武、黄胜昭、付名轻。烧窑的和制砖坯的也名列其上:卢志民、付原方。
细细揣摩、对比这两侧铭文,我有更有趣的发现。两者书体风格大不相类,“上大人”这一面是当时典型的文书体,也就是“馆阁体”,柳体楷书,略带行意。估计是书记官先生的应差之作,弥满衙署官气,可说是毫无艺趣可言。另一面可就有点意思了。看不出所宗何体,但笔划中显出率真遒劲之天趣;也不讲求规范,能简化省事的就简化,达意而已,如将“傅”写作“付”,把“盧(卢)”写作“芦”,把“伏”写作
“夫”,砖窑两字的笔划也简化了,可能是当时的民间简化字。估计出自村野土秀才之手,最多是乡间私塾先生。铭中有一叫付名轻,怪怪的,我猜这位叫名轻的“小甲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村民小组组长,可能是个很俏皮的青年工头,他似乎不情愿将自己的大名被刻在砖上送到京城,就随便地报了个“名轻”,类似现今一些文章作者喜欢用“佚名”的化名以示自谦。现在我偏要将这位600年前甘于“名轻”的阿凡提式的工佚提溜出来,告诉他“卑贱者最可贵”,你和你的数以万计的伙伴们辛勤劳作的汗水,浇灌了我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之花,你们是历史的真正的主人,你们的名字将彪炳万古,何轻之有!
199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