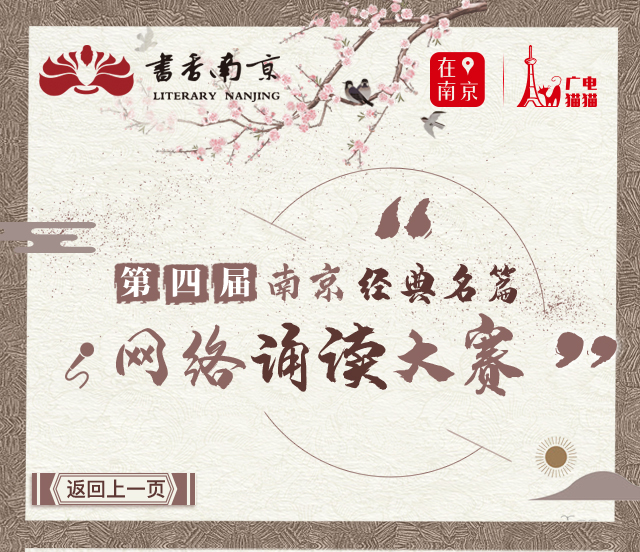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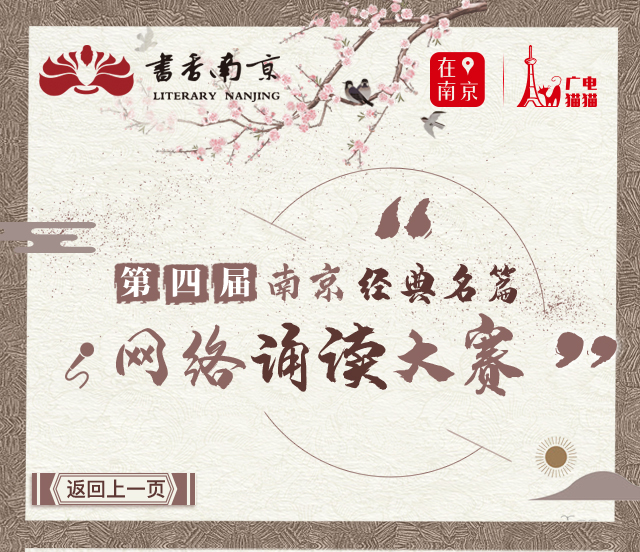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邓海南】
(本篇选自《南京大观》,作于1993年12月。作者邓海南(1955- ),祖籍江苏泰兴。诗人,剧作家。
钟山之麓,紫霞湖边,古城墙下,伟人墓前。每一条路径都通向深邃,每一片层林都折叠着幽静。作者居住在东郊风景区,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赞叹里,交织着时时闪烁出哲理之光的情思。)
路与麓
这几年,我有好些朋友都挪窝去了海南。有朋友和我开玩笑:“不叫海南的都去了海南,叫海南的怎么倒没去海南?”我笑道:“此海南不是彼海南,乃是上海的海,南京的南。”不愿舍弃南京往海南去,除了有惰性懒得动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就住在东郊风景区的边上,有点舍不下这一片风景。
细想起来,对于居住和工作来说,南京并没有太多的优点。冬天太冷,夏天太热,气候不如青岛;以古都自居,性格趋于保守,开放不如广州;经济不如上海活,机会不如北京多,街市比不上天津繁华,物产比不上成都丰富……想来想去,南京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拥有一片郁郁葱葱的、苍苍翠翠的、能让人心旷神怡而又充满了历史底蕴和帝王之气的东郊。
在东郊,随便拣一条路走进去,都是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致。你可以从中山门顺着城墙走到梅花山,也可以从太平门沿着城墙走到植物园;你可以从孝陵卫正面向着山走到灵谷寺,也可以从卫岗侧面朝着山走到中山陵;你可以从明孝陵沿着曲径上山走进紫霞湖,也可以从天文台顺着盘山道走入琵琶湖。这些都还是叫得出名目的知道能通向哪里的大路,要是你想有一份意外的惊奇与发现,就任意走进一条林间小路,让它随便把你带到哪里,结果都不会使你失望。不是空山鸟语皆幽处,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山重水复的情况当然会有的,但绝不会走到疑无路的地步。路都不会太直,也不会太平,或上或下,忽左忽右,只要不走出紫金山麓,每一条路都会使你意趣横生、兴味盎然。
我查了一下字典,麓,是山脚。是山和平地交界的地方,也是尘世和大自然交界的地方,这个交界处是一大片斜坡,这一大片斜坡被森林覆盖着,被大路和小径交织着,由寺庙和陵墓点缀着,还有湖泊镶嵌着。于是六朝古都的王气有了,林间溪头的野味有了。大自然把它的气韵向都市的嘈杂浸润,大都市也把它的繁华向大自然的宁静渗透。这里不完全是天然的神工鬼斧,也不完全是人工的精雕细刻,天然与人工,风景与文化,历史与今天,环境与心境都在这里融合在一起了。只有一大片平缓而又具有动势的斜坡才会有这种广博而深厚的气派。缺乏起伏的平野和兀然而立的山岩都不可能具备这种襟怀。东郊的魅力,或许就在这里。
墓
东郊是热爱风景的活人和许多死去的名人共享的地方。对活人来说,是好风景;对死人来说,是好风水。朱元璋的墓在这里,孙中山的墓在这里,廖仲恺、何香凝的墓在这里,邓演达的墓在这里。汪精卫的墓曾经也在这里,因为不配在这里,被炸毁搬走了;蒋介石的墓也想放在这里,因为历史的变迁而没能留在这里,这对他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不过就现有的这些陵墓来说,已经是蔚为大观。你每走近一个陵墓便是在走近一段历史,你可以触摸它、阅读它、思索它、凭吊它,并在一种恬适的心境里享受它给你带来的庄重和宁静。而墓的主人,也许还灵犀尚存,正安坐墓中背靠着钟山这把座椅在享受你的瞻仰。朱元璋的孝陵无论从规模和排场上来说恐怕比不上他的那些埋在北京十三陵的皇子皇孙们,但是开国皇帝的气度和钟山的气势结合在一起,就有了一种他的子孙们远远不及的大家风范。陵前那两条路上的石翁仲和石像,象两排历史的肋骨,紧挨着吞吐自然之气的风景区的肺腑。
孙逸仙的中山陵,可以说是所有中国伟人陵墓中最伟岸最壮观的一座了。明孝陵是掩映在山树丛中的,中山陵则坦坦荡荡地依山势横陈在阳光下,老远看去,便能看见宝蓝色的琉璃顶和长长的白石台阶,一代伟人的灵魂嵌进了一座山的怀抱。如果从陵的顶端向下俯瞰,近处的层林和远处的雾霭,统统都成了你可以用胸襟去包容的东西。但我更喜欢的还是廖仲恺墓和邓演达墓,没有那么显赫,没有那么铺陈,只是静静地坐落在一条路的尽头,一片林的中间,不知道的人会忽略它们的存在,而对于知道它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走过去,它都会给你一片别处难得有的恬淡和安详。
湖
东郊还有好几片湖。前湖是袒露在城墙边与山脚下的;琵琶湖是半藏半露地坐卧在城墙拐弯处的凹陷里的;而紫霞湖则是珍藏在钟山怀抱里的一块碧玉,你必须走进去撩开它的衣襟才能看到。
我在前湖里游过泳,面对着彼岸那一道斑驳凝重的古城墙,你会产生一种朝历史深处游去的感觉。其实那道城墙后面就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因为被城墙挡住了,你全然看不见。当你游到城墙脚下,在那巨大的阴影下踩水休息的时候,你觉得和历史只有一墙之隔,城墙的那边,依然是明朝。于是你努力向回游,对于历史,还是站得远远的回头看才好。
而在被山所环抱的紫霞湖里游泳,什么历史感、现代感、文化感都会离你很远很远,这里只有山、只有水,只有树,只有飘动的云和不动的天,只有在湖边林中呜叫的和在湖的上空飞过的鸟,你会同时具有鱼的感觉和鸟的感觉,只是没有鱼的鳞片和鸟的羽毛。如果要想肉体和灵魂同时洗个澡,再也没有比紫霞湖更合适的澡盆了。一个猛子扎进湖里,从湖面伸出头来四面一看,你会发现自己身体在水里,心灵却在山里。你已和山水融合为一,还需要寄情于山水之间吗?
树
数年前一位好友从西北来南京,我带他去东郊玩,刚一走进风景区,他就被这一大片绿色震慑住了,说他走过不少城市,没见过哪个城市的边上有这么多的树。东郊的树量多,在梅花山上向四周环顾,山上山下各种树木疏疏密密高高低低起伏有致;在灵谷塔上向下鸟瞰则是满目葱茏。东郊的树的种类也多,中山植物园就在这万绿丛中,华东一带的大多数树种在这里都可以找到样本。东郊的树风姿也和城里的树不一样,生长得格外大方舒展。同样是悬铃木,在城里的街道上弯腰屈背只为了给马路遮荫,而在通向中山陵的大道两旁则可以由着它们的天性自由地伸开臂膀,长成一种参天的姿态。你如果离开大路,从旁边去观望它们,仅只两排树竟高大茂密得俨然就是一片厚实的森林。此外春天的梅花、秋天的枫叶、风里的香樟、陵前的松柏、本地的榆槐、舶来的石楠……如果你喜欢树木的语言,东郊就是翻不尽的辞典。
人是需要树林的动物,所以在东郊才能感觉到和大自然的亲近之情。如果东郊没有山、没有墓、没有湖、没有路,在想象中都还可以接受;可要是没有这么多的树,那就鄙陋乏味得没有情致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