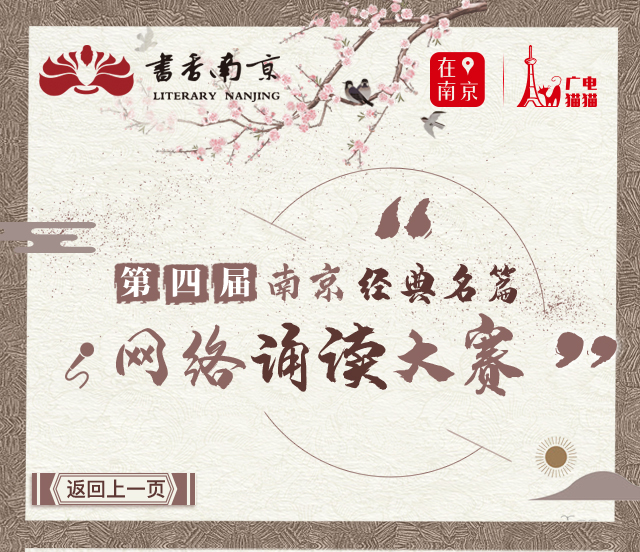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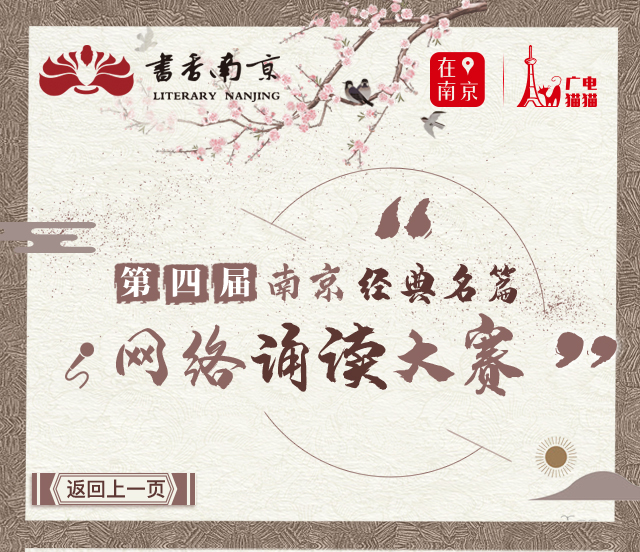

【王干】
(本篇选自《扬子晚报》(1994年5月至6月),作者王干(1963- ),江苏兴化人。文艺评论家。著有论文集《南方的文体》等。
本文原为总题《闲话南京》系列文章中的四篇短文,分别写南京的春、夏、秋、冬。收入本书时,合为一篇,题目为编者所加。作者的笔调轻松、活泼,涉及南京四季印象中的方方面面,感觉敏锐,侃侃而谈,体现出一种“闲话”文体的自然本色。)
春
南京的春,匆匆。
南京属亚热带气候,亚热带气候的特点是四季分明。南京的四季比较分明,春是春,夏是夏,秋是秋,冬是冬,可惜的是四季分布的时间长度不均匀,春秋特别短暂,稍纵即逝似的,而夏冬异常漫长。如果春秋期间到外地出一趟差,感觉上就像卸了冬装就着夏装,脱了汗衫就穿羽绒服似的。
南京人格外地热爱春天,因为它太短暂了。
南京的春天是从梅花山着陆的。我至今没有到梅花山去游览过,我知道春自梅花山还是友人信中透露的信息。这位朋友求学在外,有一年春节过后便写信向我诉说对故乡南京的思念之情,说当时特别想到梅花山去赏梅迎春,呼吸第一缕春的气息。我当时感到这意境奇美,心中暗暗记住了梅花山,但始终不敢涉足,唯恐破坏心中的圣境。就像到南京生活了七八年,我始终不知道总统府在哪里一样,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总统府是一个很高很大的地方,而现实中的存在肯定会破坏我的想象。直到去年搬到长江路来住,与总统府成为街坊邻居了,才知道总统府原是我路过了无数次的一座建筑。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记忆仍仿佛没见过总统府似的,仍觉得这是一个遥远遥远的旅游胜境。
因而,每到春天就想起了梅花山,每当有人提起梅花山就想起了南京的春,这种美好的记忆与美好的联想让我沉浸在遐思之中而暗自陶醉,有时会觉得明媚春光也洒满了绿色的稿纸,我的写作也如农民春耕一般勤奋了。
我撰写此文的时刻正是南京春的高潮同时也是春的尾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女孩在宜人的和风中轻盈的身影,她们欢乐的笑声像枝头飘落的花絮,散泛着迷人的温馨。猛想起辛弃疾的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哦,南京的春也便在蓦然回首之间。
夏
南京的夏天是全国闻名的,素有“火炉”的“雅称”。夏天除了温度高以外,持续时间也特别长。在我的印象中,每年南京仿佛有两个夏天似的,从五一节到国庆节,就离不开汗衫、短裤、裙子这些夏日的着装。夏日才是女性真正的春天,因为在炎热的气候下,女性可以卸去一切不必要的包裹和遮掩,尽情而又理所当然地展现女性形体的特有的优美,在这个时候,观念开放者与保守者穿得同样的薄,同样的少、同样的透明、同样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季节赋予她们的审美共识。
难怪南京女性的美丽度远远高于其它城市,原来她们每年都拥有“第二个春天”。
夏天则是男士尴尬的日子,它让男士大失绅士风度,西装革履不仅对自己是沉重的负担,还增添别人的炎热感。好在南京人豁达,男人们打赤膊、趿拖鞋在新街口招摇过市绝不会担心有碍观瞻,露宿街头更是家常便饭。面对酷暑盛夏,南京人犹如从太上老君炼丹炉中出来的孙行者,他们一是毫无惧色,二是有很多消暑的办法。倒是这几年夏天的暴热不像往日持续得那么漫长,南京人反而有些不自在,他们炼就多年的抗高温能力和对付炎夏的种种措施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伤,而那些刚刚购买了空调的人家更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1988年的南京的夏天是让人难忘的季节。持续的高温让很多老人和病人辞世,至今想起来还有些不“炎”而栗。当时我在北京工作,没法体会到受烤的滋味,只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里看到烈日之下一位交警后背被汗水浸湿的镜头,那是一个感人的背影,现在想起来我的眼睛仍禁不住像当初一样湿润润的。
秋
有一位朋友画家说:南京的秋天挺好写的,一个漫长的季节。
我感到很惊讶,漫长?它和春天一样短暂,当你感到秋意时,冬天已经来临。
画家听我扳着指头算完日期,又问我:那我怎么会感到南京的秋天美好而又漫长呢?
我摇摇头,随便说了一句,会不会与你们的职业习惯比如色彩感有关?
对了!画家很兴奋,对对,是色彩。你看这南京的树特别多,品种也多,秋风一起,树叶便开始断断续续往下落,最初是梧桐、泡桐的叶子,它会在你骑车时悄然落到你的身上或者眼前,它那么成熟而又那么苍老,像一个饱经风霜老人的面孔。银杏树的叶片金黄金黄的,透明得像个稚气的小男孩,一阵秋风吹过,金色叶片哗哗地像一阵清脆的童音飘落下来。
画家此时是一个抒情诗人了,越说越兴奋;还有那水杉树,像个少女似的,萧瑟秋风一起,树叶便开始有点红晕,秋风越劲,她的面庞越发通红,红得都让人心醉了。如果这个时候,你来登临栖霞山,你会置身到红叶的海洋之中,漫山遍野的霜叶红似火、胜似二月花。秋天的紫金山、秋天的中山陵、秋天的紫霞湖、秋天的牛首山,……都非常非常的迷人。秋天是写生的最好季节。
色彩的丰富让画家感到时间的长度被延伸,因为画家关注的是落叶颜色嬗变的过程,如果落叶颜色千片一律,画家只会觉得时间很短,人在审美过程中参照的是心理时间,而不是物理时间。
我则联想到整个南京城似乎都充满了秋意,紫金山、紫霞湖、栖霞山的“紫”与“霞”都与秋和黄昏有关,金陵、秦淮、建康这些名称脱不了些许暮气。悠久的历史感显然让南京城的色彩变得丰富多彩,但与只有百余年历史的上海和和只有十余年历史的深圳相比,南京是“人到中年”了,成熟、沉稳、深厚之余则渴望多一些青春的活力。怪论!城市也会像人一样么?我不禁反问自己一句。
冬
南京的冬天室内和室外一样冰冷,一样的“不近人情”,在阳光灿烂的白天,室内更显得冰窟窿似的寒意袭人。一般人可以钻到被窝里看电视、睡觉养精神,可“码字族”不能坐在被窝里写作,而写作又是轻闲活,越写越冷,越写手越僵,最后脑子也僵了。南京的冬天不是写作的季节。
我们这群写作者在冬天往往兵分两路,一支“南下”,一支“北上”。“南下”是去花城广州,一般是公费支付,大多受出版社、编辑部之邀,亦有由作协系统内部安排的,往往住星级宾馆、出入有人陪同,半休假半旅游,至于能“码”多少字则不可一概而论。“北上”是去北京,不必住宾馆,朋友的家也行,因为北京的供暖五星级宾馆与平民住的楼房具有同一水平,温度在摄氏20度左右,且室外不像广州花香鸟语而是寒气袭人,只有回到室中潜心写作。1988年冬天,我住在北京一间简陋的招待所里,两个月居然写出28万字的作品,抵得上在南京12年的写作量。那真是写作的好时光,我至今对北京的冬天充满了留恋。
我不太喜欢南京的冬天,它让人不知道干什么好,整天冷兮兮的,上班冷,下班冷,回家亦冷。冷得只想不停地吃,所以火锅热在南京久盛不衰。不是南京人好吃,而是为了取暖。
我始终有一件事弄不明白,南京和北京冬天的时间差不多漫长,温差也不大,可从11月10日到翌年4月5日,北京无论是机关还是住宅区都有暖气供应,室内都温暖如春,睡觉都只需一床薄薄的棉被,而南京人则享不到这种“暖”福,室内室外都须穿着羽绒服,睡觉时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厚厚地被封闭得严严实实,一不当心就会冻感冒,至于面若桃花、手掌红肿的冻疮患者更是屡见不鲜。据说当初是以淮河为界来确定供暖线的,且不论这种划界是否科学,即使科学的话也时过40余年而“界”迁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这道供暖线是从节省能源的角度制定的,“节约每一个铜板”都是革命事业的需要,而不是淮河以南的地区没有冬天,更不是说淮河以南的人们不需要温暖。
如今,建国已40余年,生活的质量也在日渐提高,南京人在冬天花的取暖费用并不少,空调、取暖器、油汀、煤炉等十八般“武器”全用上了,但效果显然都不如暖气,差不多都是低效应、高耗能。能不能采取北方供暖的方式让南京人、江苏人和淮河以南的人们都拥有“第二个春天”呢?
这并不是一种高消费的奢望。有了暖气,既方便了生活,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可以节省能源,至少可以缓解电力供应的矛盾。你说如何?
